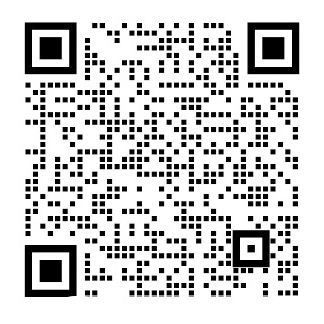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与青年的正向行为支持
Jennifer Neitzel
摘要:正向行为支持近年来在减少包括自闭症谱系障碍在内的各种残疾儿童少年挑战行为方面成为一种有效的实践。自闭症学生积极行为干预的目标是通过使用循证实践预防和减少干扰行为的发生,例如重复或破坏行为。为了实施具体的行为方法和策略,随着干扰行为变得更成问题,采用分层方法逐渐增加对自闭症学生的支持的性质和强度。在这种方法中,功能行为评估分析干扰行为的可能原因以及在全面行为干预计划的背景下实施的策略。本文旨在(a)讨论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中的干扰行为,(b)提供一个预防和减少这些行为的模型,(c)提供多种基于证据的实践,用于解决自闭症儿童与少年的干扰行为。
关键字:自闭症谱系障碍,挑战行为,干扰行为,正向行为支持,重复和刻板行为
破坏行为和其他挑战行为并不是诊断自闭症所必须的。然而,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尤其处于发展至少一种干扰其学习和发展的挑战行为的风险(Buschbacher和Fox,2003; Matson和Nebel-Schwalm,2007)。干扰行为一词通常用于指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可能表现出的两种类型的行为:(a)重复的和刻板的行为(例如,重复地来回摇摆身体);(b)破坏行为(例如,侵略,发脾气)。这两种行为都可以抑制自闭症学生有意义地参与学习活动和与他人的社交互动; 因此,限制他们获得关键社会、 沟通和学术技能的能力。
了解如何解决已经成为问题的干扰行为是家长,教师和其他从事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工作和生活的从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旨在(a)讨论自闭症儿童与青少年中的干扰行为,(b)提供一个预防和减少这些行为的模型,(c)提供多种基于证据的实践,用于解决自闭症儿童与少年的干扰行为。
正向行为支持解决干扰行为
最近,越来越强调使用积极的行为干预来改变教室或家庭环境,以防止干扰行为的发生,并教导儿童或青少年采取更适当的替代行为。研究表明,为了使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成功的教育干预,必须考虑和发展积极和主动的行为。正向行为支持(PBS)是一种常见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已经用于表现出挑战性行为的儿童和青少年。 PBS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加其适当的行为和调整学习环境来改善儿童的生活质量,以防止干扰行为首次发生或重新发生。PBS研究表明,它有效地减少有风险行为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干扰行为,以及各种残疾儿童,包括自闭症儿童。(Bushbacher amp; Fox, 2003; Carr et al., 1999; Dunlap amp; Fox, 1999; Iovanne et al., 2003;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 Turnbull et al., 2002). 在PBS中,分层干预模型通过在层级的每个层级逐渐应用更集中的支持和干预来增加儿童的积极行为(Scott amp; Caron, 2005). 图 1 说明了使用PBS 的干预层次结构的分层的性质。传统的 PBS 模型的许多元素都是有关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例如,小班授课,个性化干预措施);然而,几个方面需要进行调整,以解决自闭症的核心特征。
第三层:三级预防
针对具有高风险行为的学生建立的专门个性化系统
第二层:二级预防
针对有危险行为的学生建立的专门组织系统
第一层:一级预防
针对所有学生、工作人员环境建立的学校、课堂系统
图1.传统的积极行为支持模型
资料来源:OSEP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技术援助中心(2009年)。
首先,社会和沟通缺陷在这群儿童中很普遍; 因此,这些技能的发展是所有三层干预层级的关键重点。可能难以确定儿童或青少年是否参与干扰行为,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式来传达他们的需求和需求。 因此,教师和其他从业者必须设法通过进行功能行为评估(FBA)来识别可能导致干扰行为的环境中的因素。在传统PBS模型中,FBA通常在第三层中启动; 然而,FBA是在这个模型的第2层为儿童和青少年ASD启动,所以教师和其他从业者可以准确地识别环境、感觉和社会交流变量可能引起干扰的行为。这个问题解决过程帮助教师和家庭识别干扰行为(即,环境中什么导致和加强行为)以及可用于最终减少其发生后续的作用。图2说明了传统PBS模型如何适应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
虽然这两种模式都使用分层方法来提供从最少到最密集的行为干预,但可能有必要为一些学生立即提供密集和个性化的干预,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 。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的分层干预方法包括预防策略,功能行为评估和综合行为干预,旨在减少干扰行为,增加积极行为和适应性技能(国家研究理事会,2001年)。
在每个干预层面,重点是通过团队建设和家庭参与确保积极的关系。 个体家庭成员的福祉被认为是自闭症儿童和青年发展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特别是在第3层,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必与家庭成员合作一起发展支持家庭功能和福利的干预措施,并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中保持一致(Dunlap&Fox,1996)。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们将重点概述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的PBS模型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可用于预防和减少这种儿童群体干扰行为的循证实践。
一层:预防措施
层 1 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干扰行为的发生。这一目标通过改变环境、 活动和其他可能引起干扰行为升级的相互作用等具体的预防性措施,旨在解决自闭症的核心特征。(Buschbacher amp; Fox, 2003; Sharma,Singh, amp; Geromette, 2008). 它们包括(a)组织高质量的学习环境,(b)安排环境以支持积极的学生行为,以及(c)发展沟通和社会技能作为核心课程的一部分。
二层:基于功能评估的干预
尽管在第一层中已经实施了预防措施,PBS模型的第2层或二级预防,旨在为那些继续展示干扰行为的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可能需要在第2层中提供额外的不是很危险的支持行为;然而,尽管实施了预防策略,它们仍然继续发生。第二层侧重于三个结果:(a)使用功能行为评估来设计一个指导干预的全面行为计划,(b)在正在进行的常规和活动中实施循证实践,以减少干扰行为,(c)进一步发展沟通和社交技能。 这些活动与传统PBS模式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为什么与自闭症发生干扰行为并不总是明显的。 因此,教师和其他从业者必须进行功能性行为评估,以确定干扰行为的功能,以便选择适当的循证实践来减少和替代该行为。第二,小组教学(如传统PBS模型的第2层中经常使用的那样)可能不总是适用于自闭症学生的干扰行为,同伴分组可能加剧一些学生的问题。 重要的是,干预措施是个体化的,以满足每个自闭症学习者的独特需求和特征,从而可以快速有效地减少干扰行为。
三层:密集、个性化的干预措施
尽管使用第1层和第2层采用的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但这些学生继续表现出干扰行为,因此,第三层的重点是为自闭症学生提供强化的个性化教学。当教师达到这一层次的支持时,干扰行为已经成为问题。 例如,行为可能几乎持续发生,或者它们可能对学生或其他人具有潜在危险(Scott&Caron,2005)。在第2层中使用过的一些活动也可在这个阶段使用;然而,他们更个性化和集约化。 例如,教师和其他从业者使用功能性评估来制定正式的行为干预计划,实施更强化的干预措施以减少干扰行为,并更频繁地监测结果。
近年来,正向行为支持作为解决ASD中儿童和青少年干扰行为的有效方式已获得关注。这种做法对这一人群的干预特别有前景的,因为它强调通过基于高质量功能行为评估的结果提供越来越强的干预来预防干扰行为并减少其发生。通过使用预防性和专门的教学实践和策略,支持自闭症学生的积极行为,能更有效地解决干扰行为。
正向行为支持的描述性年度报告
格伦丹拉普·南佛罗里达大学
爱德华·G·卡尔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发展 残疾的研究所
罗伯特·H·荷马 俄勒冈大学
罗伯特·L·格尔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韦恩水手 美国堪萨斯大学
雪莱克拉克 南佛罗里达大学
林恩格尔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理查德·w·阿尔宾 俄勒冈大学
博比·j·沃恩 南佛罗里达大学
达琳·Magito·麦克劳克林 正向行为支持咨询
金马伦詹姆斯 发育障碍研究所
安妮·w·托德 俄勒冈大学
j·斯蒂芬·牛顿 俄勒冈大学
约瑟夫Lucyshyn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彼得·格里格斯 堪萨斯大学
汉克·博安侬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
桢勋崔 美国堪萨斯大学
劳丽·Vismara 加利福利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曼迪Boettcher Minjarez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Pamelazita Buschbacher 南弗罗里达大学
丽瑟·发科斯南弗罗里达大学
专业:特殊教育 学生姓名:黄双凤
指导老师姓名:王薇
摘要:正向行为支持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适应性行为得到广泛、长期的改善;然而,目前的实证基础表明,正向行为支持主要是在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对短期研究。因此,需要一个可靠的数据存在,来告知我们正向行为支持在自然社会环境中执行较长一段时间对全面的生活方式这个领域的影响。目前的调查是为了提供一个PBS多年的参与者和广泛的测量策略的描述性分析。使用广泛的数据组合21名参与者,我们采用评级量表来量化从基线到2年干预的关键变量的变化。数据揭示变量水平的干预完整性,广泛减少问题行为与偶发性复发,并鼓励在六个生活质量领域的增强。这项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通过记录整天,整年,所有环境中的行为模式来了解行为支持的过程和结果。为了有效、可持续的积极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我们讨论决定需要考虑新的概念和方法框架。
正向行为支持(PBS)是一种用于提高生活质量(QOL)和解决行为问题(Carr et al.,2002),近年来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支持和普及的方法(Carr et al.,1999;Dunlap amp; Hieneman, 2005; Sailor, Dunlap, Sugai, amp; Horner, 2009)。积极的行为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作为一套干预策略,可用于所有社区,家庭和学校环境,以解决严重的问题行为,而不诉诸于痛苦或耻辱的程序。它被设计为一个积极的方法,通过它,增强个人的能力,将导致丰富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其次,减少严重的问题行为。正向行为支持源于应用行为分析,并且仍然附属于这一核心学科,尽管它也借鉴了其他传统、 学科和方法(Dunlap, Carr, Horner, Zarcone,amp; Schwartz, 2008)。正向行为支持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了解控制个人行为的变量来改善个人的生活质量,然后使用该理解来教导个人控制他或她的环境和重新安排环境的新技能,使其更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亲社会的反应(Bambara amp; Kern, 2005; Janney amp;Snell, 2008)。
在过去十年的一些出版物中总结了关于正向行为支持的实证支持(e.g., Carr, Horner, et al.,1999; Dunlap amp; Carr, 2007)。本质上,这些综合表明,(a)功能评估的过程有助于识别问题行为的功能和控制变量,并且功能评估的结果可以用于增强随后干预的疗效。(b) 教学替代技能是减少问题行为的有效策略(e.g.,Carr amp; Durand, 1985; Halle, Bambara, amp;Reichle, 2005)。(c)在功能评估数据的基础上改变前因变量可以快速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Luiselli, 2007)。(d)基于功能评估的多元正向行为支持干预措施已经在几项研究中显示与减少问题行为和增加替代的、期望的应答相关(e.g., Carr, Levin, et al., 1999)。这些调查结果只是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正向行为支持实践的其他要素具有较少的研究支持,一般是基于广泛的临床经验,一些评价数据,以及偶尔的实验或准实验研究。这些做法包括评估情境变量,使用以人为中心的规划,以及将事件设置为干预的一个组成部分(Dunlap amp; Carr, 2007)。
虽然对正向行为支持的核心组件的经验支持是公认的,但许多作者已经描述了现有数据库中的重要限制(e.g., Dunlap amp;Carr, 2007)。也许最明显的限制是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已经涉及限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段 (例如,3-5 个月) 的观测和局限于只有一个或两个良好的控制设置。由于研究设计的狭窄,这些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们与改善生活质量的目标不一致,该目标涉及一个人的存在的全部宽度,在一天的所有设置和时间以及多年的时间, 而不是通常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干预研究(Hughes, Hwang, Kim, Eisenman, amp; Killian, 1995; Schalock, 1990)。
有一些明显的例外, PBS干预措施已经在一段时间内以全面的方式实施(e.g., Lucyshyn et a I.2007)。例如,Feldman, Condillac,Tough, Hunt, and Griffiths (2002) 对20名发展障碍的个体进行了研究,他们表现出严重的问题行为,如自我伤害和攻击行为。他们执行了一个正向行为支持协议,包括功能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 Descriptive, Multiyear Examination of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ABSTRACT:: A major goal of positive betiavior support (PBS) is to produce broad-based, long-term improvements in adaptive behavior;howeve,, the empirical base,, at present,is mainly composed of relatively short-term studies carried out in circumscribed contexts. Therefore, a need exists for reliable data that can inform the field regarding the comprehensive lifestyle effects of PBS implementation in natural community contexts ove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The current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provide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BS with diverse participants and broad measurement strategies over multiple years. Using extensive data portfolios for 21 participants, we employed rating scales to quantify changes in key variables from baseline through 2 years of intervention. The data revealed variable levels of intervention integrity, generalized reductions in problem behavior with occasional relapses, and encouraging enhancements across six domains of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represents an initial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behavioral support by documenting behavioral patterns across full days, entire years, and all environments. We discuss the need to consider new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further study of efficacious and sustainable behavior support.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BS) is an approach for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resolving behavior problems (Carr et al.,2002) that has gained considerable empirical support and popularity in recent years (Carr et al., 1999; Dunlap amp; Hieneman, 2005; Sailor, Dunlap, Sugai, amp; Horner, 2009).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emerged in the mid-1980s as a set of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at could be used in all community, home, and school settings to address serious problem behaviors without resorting to painful or stigmatizing procedures. It was designed as a proactive approach through which enhancements of an individuals competencies would lead to an enriched and more satisfying life and, secondarily, to reductions in serious problem behaviors.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evolved from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nd remains affiliated with this core discipline, even though it also draws from other traditions, disciplines, and methods (Dunlap, Carr, Horner, Zarcone,amp; Schwartz, 2008). The primary goal of PBS is to improve an individuals QOL by ga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ables that govern an individuals behavior and then using that understanding to teach the individual newskills for controlling his or her environment and rearranging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o support desirable, prosocial responding (Bambara amp; Kern, 2005; Janney amp;Snell, 2008).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PBS has been summarized in a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e.g., Carr, Horner, et al.,1999; Dunlap amp; Carr, 2007). In essence, these syntheses demonstrate that (a) the process of functional assessment is useful for identifying the function of and controlling variables for problem behavior and that the results of functional assessment can be used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subsequent interventions, (b)teaching alternative skill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educing problem behaviors (e.g.,Carr amp; Durand, 1985; Halle, Bambara, amp;Reichle, 2005), (c) altering antecedent variables on the basis of functional assessment data can rapid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roblem behaviors (Luiselli, 2007), and (d) multicomponent PBS interventions, based on functional assessments, have been shown in several investigations to be associated with reductions in problem behaviors and increases
in alternative, desirable responding (e.g., Carr, Levin, et al., 1999). The findings just summarized are based on considerable data from numerous investigations. Other elements of PBS practice have less research support but are based on extensive clinical experience, some evaluation data, and occasional experimental or quasi-experimental studies. Such practices include the assessment of contextual variables, the use of person-centered plann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setting events as a component
of intervention (Dunlap amp; Carr, 2007).
Although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core components of PBS is acknowledged,
many authors have described important limitations in the existing data base (e.g., Dunlap amp;Carr, 2007). Perhaps the most conspicuous limitation i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relevant studies have involved observations restricted to relatively short periods of time (e.g., 3-5 months) and confined to only one or two well-controlled settings. These limitations are understandable given the strictures of research designs, but they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QOL, a construct that pertains to the full breadth of a persons existence, across all settings and hours of the day, and for periods of years, rather than the usual weeks or months of intervention research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