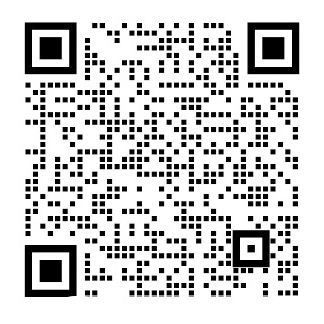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故事'与'情节'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中如何运用两个重要的叙事学概念,试图发掘叙事技巧在抒情诗批评中的潜力。首先发现抒情诗中的寓言既包括物质元素,又包括抒情元素;其次,对汉语诗歌的解读不仅需要理解文本中所呈现的事件,还需要理解诗人的超文本背景;第三,对抒情诗空间的理解需要对故事、话语、诗人的创作过程以及读者的参与。本文从认知诗学的角度认为,对抒情诗的完全审美认识需要读者的想象力、知识、精神状态和文本。最后,本文在分析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时强调,读者对诗人生活的认识至关重要,可以作为理解中国抒情诗的务实方法。
关键词:叙事学 |故事 |情节 ·空间 |中国古典诗词导论
叙事理论、概念和词句除了合法应用外,还越来越多地被导入到抒情诗的诠释和分析中。正如Klimek所主张的,大量关于诗歌分析的文献与'新叙事学'的见解相结合,采用了所谓的克拉斯-原文叙事术语(2013年,第220页)。法布拉和舒泽是叙事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在她关于叙事学的开创性作品中,Bal认为'fabula是一系列逻辑和时间相关的事件,从一开始就似乎排除了读者的情感介入'(2009年,第194页)。而'朱杰特'被查特曼定义为叙事的'话语'层次(1978年,第19页)。本文作者在对这两种叙事概念的传统理解的基础上,认为叙事中的法布拉和柔志概念化应与读者的情感投资相结合。此外,读者对寓言的诠释对于欣赏文学作品至关重要,无论流派如何。
作者的论点与沃尔什对法布拉的解释一致。沃尔什指出,所谓的fabula是'一种伴随读者与叙事话语谈判并服务于读者谈判的解释性结构'(2007年,第52页)。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与布布拉和朱泽特有联系。沃尔什引用Iser(1989年,第9页)的话,认为文学文本存在'空白',例如'情节线索'或事件之间的'空白',读者必须填写这些空白,才能将各种文本元素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2007年,第52页)。此外,本文的作者声称,如果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虽然法布拉在叙事或诗歌的抒情和叙事特征,它有不同的强调在这两个流派:在小说的fabula强调叙事,而在诗歌中,法布拉则涉及抒情。文学综述表明,虽然对法布拉和舒哲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但在抒情诗的叙事方面做得很少,对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法布拉和苏哲则知之甚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试图通过引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实例,探讨这两种叙事手段在抒情诗中是如何实现的。本文提出了两个问题:
1. 抒情诗中,法布拉和苏哲是什么样的?
2. 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这两种叙事概念的特点是什么?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作者首先探讨了抒情诗中法布拉的一般特征,然后考察了中国历史诗词中法布拉和舒哲的双重性。最后,通过对《诗经》的仔细分析,论述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柔志'所创造的空间。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拓宽除小说作品外,在其它流派中应用纳拉托洛基-卡尔概念的研究范围。本文还可能为中国古典诗词叙事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寓言中的叙述性和抒情性 结构学家用来将每个叙事文本定义为双折式,由 fabula(故事)和sjuzhet(话语)组成。在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1978年)中发展起来的叙述中,故事(主持人)是事件的内容或链条(行为、事件)加上所谓的存在(人物、设置项目),而话语是表现力内容传递方式(1978年,第19页)。在叙事学中,话语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物质和形式(Prince 2003,第21,93页)。实质是指口头或书面语言,甚至是移动图片或手势,而形式则连接一组叙述性陈述,不仅讲述故事,而且阻止情节和事件的呈现顺序。此外,本文作者从读者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任何文本的寓言都必须反映读者的情感及其价值判断。以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为例,大多数现代读者都会认为安娜的爱情是不道德的。因此,fabula不仅包括原材料,还包括读者的情绪和价值判断。
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通常注重叙事文本的叙事性和抒情文本的抒情性。小说读者期望阅读一部从事业开始的完整故事作品,然后充分发展,达到高潮,最后到达终点。对于抒情读者来说,他们往往理解哲学,希望被美学诗所感动。兰瑟曾经指出,抒情诗的读者如此倾向于拥有非叙事性的思想、感觉和视野,当事件对诗人思想的理解不深刻时,它们就会滑向'下述通知'(2008年,第235页)。弗里德曼在散文《女性写作叙事的抒情颠覆: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情节的暴君》中,强调了抒情诗和叙事的区别,她认为叙事以故事为中心,歌词侧重于精神状态,尽管每个模式包含另一个模式的元素(1989 年,第 164 页)。在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还强调,叙事被理解为一种模式,它呈现一系列在空间和时间中动态移动的事件;至于抒情诗,它是一种同时呈现一致的方式,一组情感或想法,投射出停滞状态(同上)。
抒情诗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古典诗词是抒情诗中突出的分支之一。中国诗歌中的寓言通常包含两个元素——事件和情感。一般来说,叙述是故事中的材料,这种材料是稳定的,可以通过sjuzhet恢复。叙事元素在中国诗词中很常见,如《长恨歌》(唐代白居易的经典诗作,公元618~907年)。与小说一样,中国古典诗词通常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由于诗歌结构松散,读者不易理解。如上所述,诗歌的重点是抒情,读者阅读诗歌的真正目的不是故事,而是情感、情绪和事件的印象。因此,当我们谈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寓言时,我们不仅要看事件,还要考虑诗歌中的情感。例如,在李白的《劳劳亭》中,可以通过语言获得故事: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劳劳亭》,李白,翻译为舒玲红)
《劳劳亭》是唐代李白写的五字四字曲。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不在于描绘劳劳亭所在的春天风光,而是表达诗人对离去的哀思。诗人不是选择直接表达他对离去的情感,而是通过描述告别的地方来讲述他的悲伤。他写这首诗的技巧很容易被读者察觉。读者可以通过消化传达主题的最后两行来感知诗人的强烈情感。诗人用描绘春天的微风和柳树来表现他的悲伤,这是传统的离开象征。 Tyrkkeacute;声称,万花筒叙事不是被解读为预定的线性情节,而是提供了进入事件或剧集的替代途径,将情节的构建留给读者选择(2008年,第285页)。因此,可以说,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劳劳亭》中的寓言可以解释为:(a)诗人碰巧看到劳劳亭,由于遗址的特殊性,他用他的想象国家写下了一首诗; (b) 离开时,诗人和他的朋友来到劳劳亭,他写了一首告别诗来表达他的感情;(c) 诗人听说了劳劳亭,用他的想象力写了一首告别诗。因此,可以断言有三种类型的解释,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有道理的。
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如果考虑到抒情诗的叙事性和抒情性,读者在欣赏诗歌时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获得诗歌作品的多元诗意效果。抒情诗中有许多空白,等待读者用自己的参与来填补。当诗歌的读者以个人的理解来诠释作品时,诗篇就变得多样化了,任何单一的寓言都无法从'juzhet'的台词中提炼出。正如陈词滥调一样,在一千名观众的眼中,一首诗的读者可以无数次地解读。以齐人古典诗为例,这首诗展现了它的双重性。
抒情诗和双重叙事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历史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和珍惜。中国人从自己的亲民知识中解读社会事件是中国人的传统。此外,历史写作也成为许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表达个人情感的理想手段。但是他们更喜欢描绘历史事件,而不是展示他们的感受。史学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种独特的流派。朱镕基将这一类历史诗定义为《毕节诗》。朱先生认为,毕节诗主要有四种类型:历史、仙女、爱情、对象。当诗人用四种'毕'之一来描述历史事件时,他们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经过仔细的考试,在感情的表达上有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就中国诗词而言(关于历史事件的诗词),这类诗歌中的对象可以是历史事件,也可以是讨论事件,但台词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在从死亡层次和话语层面分析中国历史诗歌后,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历史诗歌通常具有双重含义:死亡层次与历史事件有关;但在课程层次上,作品表达了诗人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读者如果能掌握诗人动机的背景知识,就能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黄云认为,历史事件虽然是历史诗的主题,但它不仅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叙事,而是关注这位诗人的思想、理想、思想和感情(1994年,第35-39页)。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歌颂历史上的英雄,有的表达政治信仰,有的讽刺或批评社会,有的对与诗人有相似经历的历史人物进行讽刺或批评。辛利说,中国诗词可以看作是一个比喻,融合了诗人的亲信、知识和情感,与诗人的经历和历史背景有关,具有现实意义。
唐代诗人陆翔在作品中提出,中国诗人会选择通过批评历史英雄或在其诗歌中评论历史事件来表达个人观点(第357页)。这意味着诗歌中的历史事件包含双重含义。在现代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诗歌的背景,因此他们有时只能品尝到文本的表面意义。中国诗词最显著的特征是双重性。
左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写'诗词'的人。虽然他才华横溢,但他对他卑微的出身感到沮丧,对血统制度感到沮丧。在他的一部关于古代历史的著作中,他描述了一朵生长在深山中的美丽花,象征着年轻的天才无法引起皇室的注意。诗人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左己的作品表达了他的情感,为中国诗人将符号和自己的情感联系起来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曹植的《怨歌行》就是另一个例子。这首诗赞美周公爵,虽然非常忠诚,但被周王抛弃,被其他朝子所憎恨。如果读者了解曹植生活的时间,他们也许会获得这首诗的深刻含义。还有更多的例子。唐代诗人陈子昂也写了一首名为《燕昭王》的诗: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这首诗讲述了战国时期(453–221年)国王如何寻找合格人才的故事。它起初没有直接提到提交人本人,也没有明显的论点和意见。这首诗的词似乎模棱两可。然而,如果读者熟悉燕金平台王的故事,而当时建安县一些高官对陈子昂感到沮丧,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背后的意思。诗人在前四行中哀悼国王的去世,后两行他供认,他的雄心壮志在现实生活中被扼杀了。在这里,过去和现在相互碰撞。诗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就像一层淡淡的薄雾,逐渐扩散和感动读者。这首诗没有详细叙述历史,而是对人物和地点进行了必要的介绍。它终于回到了令人失望的现实,其中作者无法实现他的理想生活。以黄金平台为标志,作者自己的理想,时空的距离交织在一起。通过了解陈子昂的个人经历,读者对诗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学者孙总结认为,要理解中国诗词的深刻内涵,往往需要参考古代史料、当代现实、诗人经历、读者对历史和诗人的感知,这是一部四个因素的合成(第14页)。
《咏怀古迹五首》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下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咏怀古迹五首》,徐元忠翻译)
从读者的角度看,诗歌的双重含义可以从其话语中获得。从字面意思上,读者可以感觉到昭君出生在一片繁荣的土地上,却死在荒芜的沙漠中。她对家乡怀有强烈的怀旧之情,诗人对她表示同情。诗的深层意义也可以解释,昭君的命运是诗人自己命运的隐喻,因为诗人本人也远离家乡,他喜欢的智者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两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如果读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话语上,却对杜甫传记缺乏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得出第一个结论。然而,如果读者对杜甫的人生经历了解得好,对中国诗词有了解,就会感受到诗歌的第二层次意义。同样,无论读者如何阅读作品,诗人的情感是明显的,这是不言自明的。诗人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深切向往和对未来政治生活的沉溺。
使用隐喻的抒情诗特征。诗词线通常传达两层含义,这是中国抒情诗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古典诗词的双重意义存在于语言的模糊性上,也存在于诗人打算讲述的故事中。诗人选择在实物描绘的伪装下表达他们纠结的情感,从而创造出双重意义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中的寓言就像一个谜语,既是一个谜语,也是对谜语的回答。如果读者对这首诗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者对诗人的经历一无所知,就无法理解和理解这些词背后的意义。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结构,其表面和深层意义有其自身的功能。通过话语表达的历史诗的表面意义,吸引读者欣赏语言之美;而深刻的意义则邀请读者与诗人产生共鸣。 如果读者缺乏背景知识,就不可能理解一些中国诗歌,因为读者对诗歌的感知可能会因词背后的模糊隐喻意义而受到极大的阻碍。例如,朱庆余(唐代诗人)写的一首诗就是好例子: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近试上籍水部》,朱庆余,翻译匿名)
读了这首诗,一个清晰的故事浮出水面:一位新婚夫妇在婚礼后的第二天就穿上了衣服,因为她急于得到姻亲的青睐。她担心眉毛上的妆容,于是她问丈夫是否合适。有趣的是,如果提供这首诗的背景,有第二行供读者跟随欣赏这首诗。这首诗是在诗人参加帝王考试的前夕创作的(唐代,公元825年)。当时,在参加入学考试之前,考生写诗颂扬自己的时间,希望吸引考官的注意,这是例行公事。朱庆余将他的诗献给了负责水利工程的部级官员詹吉,朱成功赢得了官员的青睐。张吉,政府官员精通诗意的台词,乐于帮助年轻人才。在诗中,张将自己比作一位新婚夫妇,把考官比作新郎。通过询问丈夫的妆容,新娘表达了她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并期望知道她是否能满足新姻亲的苛刻要求。这首诗的深刻刻板并不含糊,读者可能会看到一位有前途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皇室的青睐。沈说,在中国诗词中,诗人在作品中用配偶关系作为隐喻,表示皇帝与人的关系,或师生关系,是诗人常用的手法(沈2004,第892页)。对于读者来说,他们会被吸引去欣赏诗歌中的话语和情节。
以新批评的标准来看,以历史或诗人经验为参照的诗歌阅读只是研究诗学作品的一种可选方式。布鲁克斯在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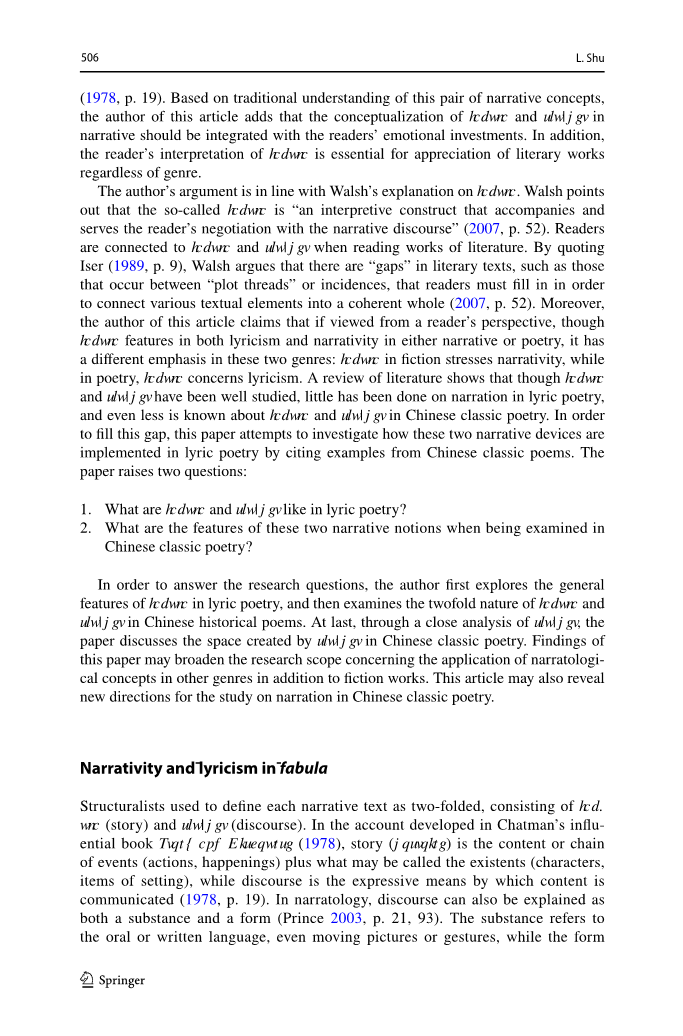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2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208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