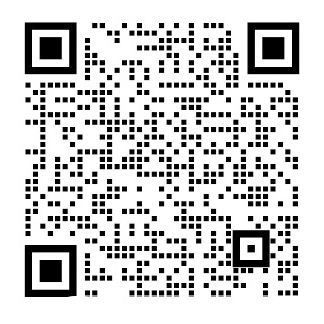家庭学校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摘要: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要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我们就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本章中,我们将从过去的主题、现在的主题和现在的主题,以及对这些主题在后现代未来的发展可能中考虑。因此,本章的一个目标是将对未来方向的讨论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为此注意将给予经济力量促使教育和社会变革,组织结构和过程发展适应经济力量,这些对于孩子在学校的教育和学习,以及我们的信仰、心理和教育干预的影响。
关键词:家庭; 学校;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现代; 后现代
本卷的章节对与当前和未来的家庭学校伙伴关系相关的几个重要主题有显著的共识:(a)家庭学校伙伴关系对优化儿童的教育经验至关重要;(b)生态发展系统的理论视角是一个有用的框架,可以概念化家庭和学校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c)多样性是国家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公立学校学生人口的特征,对教育企业的各个方面作用都很突出,包括家庭-学校-社区伙伴关系;(d)循证实践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在有效的家庭-学校伙伴关系方面的基础知识仍然有很大的限制。作者的声音和愿景是引人注目的,使信任的预测韦斯和斯蒂芬(这卷),我们准备通过国家在教育和社会政策利用关键的机会,“实现愿景战略、全面和持续的系统的家庭、学校和社区伙伴关系,显然有助于孩子的发展和学校的成功”(p449)。
尽管作者在这本书中明显达成的共识是对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改善家庭学校伙伴关系充满希望,但这一愿景也存在障碍。韦斯和斯蒂芬明智地警告说,实现这一愿景将需要重大的政策和实践的改变,以及进行、使用和交流研究和评估的新方法。此外,家庭与学校的合作还存在心理上、结构性上和历史上的障碍(克里斯蒂森和谢里丹,2001年)。
概述
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要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我们就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本章中,我们将从过去的主题、现在的主题和现在的主题,以及对这些主题在后现代未来的发展可能中考虑。因此,本章的一个目标是将对未来方向的讨论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为此注意将给予经济力量促使教育和社会变革,组织结构和过程发展适应经济力量,这些对于孩子在学校的教育和学习,以及我们的信仰、心理和教育干预的影响。
过去:现代时代的兴衰
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心理和社会服务出现在19世纪早期,这个时代与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重要的是从这里开始。尽管历史时代之间的变化是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和哲学)。驱动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或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变革。现代时代的开始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有关。工厂以其集中控制、自上而下的层次关注、大规模生产和工人作为一个可替代的部分,是现代工业时代组织结构的缩影。由于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劳动力,工厂也成为了现代教育的典范。
伴随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发生了巨大的哲学和社会变化。在哲学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从一个由灵性和信仰组织的世界转变为一个由理性、经验主义、机制和唯物主义组织的世界。世界开始被视为一个可以通过仔细的研究来理解合法的因果关系现实的地方,一旦被理解,自然最终就可以得到控制。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半熟练的、集中的劳动力;因此,有大规模的移民从农村地区到有工厂所在地的城市地区,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移民和城市化产生了需要采取解决办法的社会关切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立法中很明显(例如:童工法,强制性的学校出勤率),学校课程(例如:公民学课程,标准课程),以及学校中社会服务的诞生。
社会工作、学校护理和学校心理学的帮助职业,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实践的种子,都植根于社会关注的土壤,伴随着20世纪初与工业化和移民有关的广泛变化。城市生活的悲惨和拥挤的条件,假定的家庭破裂多代关系被打破与移民和移民,以及文化的冲突的特定民族移民,所有都引起了严重的焦虑和关心儿童和家庭的福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社会工作者早在生态心理学、系统理论或家庭治疗被引入之前就期待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态治疗。如Nichols(2008)所述:
世纪之交的社会工作者很清楚精神病学花了50年取得进展——家庭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单元。Mary Richmond(1917)在她的经典著作《社会诊断》中,为整个家庭开出了治疗,并警告不要将家庭成员与他们的自然环境隔离开来。(p19)
Nichols引用了Bardhill 和 Saunders(1988)的话,说道:
她用一组同心圆来代表不同的系统层面,从个人到文化的不同。她的实践方法是考虑所有干预措施在每个系统水平上的潜在影响,并理解和使用系统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用于治疗。(p19)
50年后,在世纪之交种植的生态实践种子开花结果了。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后来融入生态发展系统理论,是家庭-学校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出现在二战后的时代。以下对这些理论的讨论来自于Nichols(2008)。系统理论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由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发展起来的机械和生物单元的结构和功能模型。生态心理学起源于Kurt Lewin在1940年代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场论,从格式形心理学对更大的领域或整个群体的关注(Lewin,1951)。例如,Lewin提出,群体行为的改变需要解冻——这将改变群体的信念,让他们为改变做好准备。生态心理学和系统理论被Urie Bronfenbrenner(1979)优雅地整合并应用于儿童的发展中。虽然家庭-学校伙伴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Bronfenbrenner的生态发展模式上,但以家庭为中心的学校治疗的根源已经嵌入在家庭系统治疗中。虽然有许多分散的种子当代模型的家庭治疗,父亲通常被认为是Nathan Ackerman,儿童精神病学家去记录早在1938年表明研究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是理解的关键干扰的成员。家庭治疗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许多治疗模式的开花结果(见Nichols,2008年)和它们在儿童学校问题上的应用(Fine amp; Carlson,1992)。以家庭为中心的治疗的重点不断扩展到更广泛的背景水平(Nichols,2008)。家庭治疗师最初将他们对障碍的看法从个人转移到家庭,首先关注围绕问题的行为互动序列。其次,人们认识到,重复的行为序列是对家庭结构的隐喻;因此,结构成为了变化的目标。结构开始被认为是受到一个由信仰系统控制的多代过程的影响。因此,目前的家庭治疗模式强调信仰系统,这被认为是嵌入在文化中的。
当代以学校为基础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治疗模式的种子,如EcoFIT(Dishion amp; Stormshak,这卷),毫不奇怪,也在过去种植,随着家庭治疗师将他们的治疗模式推广到学校。Aponte(1976)率先进行了生态结构的家庭学校访谈,这是一项进行在学校与出席学校转诊诊所病例的家庭和学校工作人员的联合初步面谈。在20世纪80年代,阿克曼家庭研究所与纽约市的学校合作,发起了家庭-学校合作项目(由Howard Weiss),目的是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解决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Weiss amp; Edwards,1992)。
教师们学习的是常年师生会议的重组版本,称为家庭学校会议,其中包括参加与家长和老师一起参加的会议的学生。还实施了一次为遇到学校问题的儿童举办的家庭-学校问题解决会议,使家庭(父母、儿童和兄弟姐妹)与学校(教师和其他相关学校人员)一起共同讨论和确定儿童问题的解决办法。据报道,1990年该项目在50多所学校实施(Weiss amp; Edwards,1992);然而,无法找到关于其现状或有效性的数据。
总之,家庭学校干预的生态发展方法在现代出现了,但并没有牢固地扎根。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疗法的先驱者的热情和梦想以及支持者的家庭学校的系统干预都没有实现。在整个现代时代,家庭和学校仍然是自治的功能系统,在角色和责任上有明确的、可能是严格的边界(Christenson amp; Sheridan,2001)。也许儿童的教育和社会问题继续由学校充分管理;也许这些生态系统方法不被认为是儿童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也许气候还不适合改变习惯做生意的方式。或者,正如Nichols(2008)所指出的,“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对体内平衡的强调,以及家庭作为机器的控制论隐喻,如何导致治疗师更像是机械师而不是治疗师”(p20).措辞反映家庭学校伙伴关系,我们可能会说,“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学校的现代组织结构和流程与其强调专业培训和分工导致教师的教育专家和建议与父母比一个真正的合作者。”
现在:早期的后现代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后现代世界,这在商业、艺术、建筑、哲学、文学、宗教、政治、心理学和教育的变化中都很明显。在字面上,后现代时代被定义为“在现代主义之后”。这种缺乏对一个更清晰和特定的范式的引用是很有趣的。目前,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现代主义信仰、价值观和组织结构的攻击,而不是对新范式的广泛采用。而20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给社会觉得真理和科学法律可以通过客观观察和测量,后现代主义不仅问题的有效性现有科学、政治和宗教真理,也认为现实非常复杂,通过主观镜头,和质疑绝对真理是否可以知道。
后现代时代的经济驱动力,当然,是技术进步在信息处理和通信,整个国家经济从生产商品的生产知识,和业务的概念已经从本地或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和市场。
伴随我们经济基础的变化的是商业组织结构的变化,类似于我们进入现代时代,正在给现有的现代组织结构和教育过程施加压力。后现代组织的特征见表18.1。后现代时代要求实现以下几点:灵活的生产;分散的权力和控制;开放的信息共享;多技能和授权的工作团队,具有内在的个人奖励、团队激励和生产控制;对多样性和多重声音的重视;关注内部和外部的
表18.1现代世界与后现代世界的比较
|
经济基础 |
现代 |
后现代 |
|
工业 |
知识 |
|
|
组织结构 |
层次;官僚;集中控制;效率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而提高;同质性是力量;多样性被容忍;权威、培训和信息位于顶端; |
平坦,水平,几层;多技能工人的团队;效率随着专业化而下降;多样性和许多声音是一种资产;控制和权力是分散的;以内部和外部客户为中心。 |
|
组织流程 |
大规模生产、垂直规划、培训、权力和信息、外部奖励和惩罚、大量程序和规则、个人激励、生产线末端检查、测量结果标准。 |
灵活生产;水平规划;团队授予领导的权力;给予所有人的信息;内在的、授权的、工作所有权;团队激励。测量过程标准。 |
|
主导话语/哲学 |
机制与唯物主义:经验、理性、真理、与经验主义的价值;主体/对象的二元性、机械的因果关系;西欧 |
动态性;系统与环境的共同演化;混沌与复杂性;理论、社会建设、科学与伦理的融合;多元文化 |
|
教育 |
工厂模型,适合所有人。 |
个性化的选择 |
|
社会力量 |
移民、城市化、同化 |
移民;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 |
|
干预 |
以问题为中心。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和僵化的、无生产力的模式。专家角色;隐藏的信息;坚持一种特定的治疗模式 |
重点是优势。共同构建意义和小的变化;协作;信息共享;针对人群和问题量身定制的治疗。 |
客户满意度;并关注过程测量标准。这些想法在教育结构中注入的证据,可以通过多种教育选择的发展中看到,如替代学校、学校内的学校、特许学校、家庭教育,以及替代教师培训和认证途径的发展。
后现代时代的主要话语包括社会建构主义、混沌理论、女权主义哲学、环境哲学和应用伦理学(Carpenter,2008)。
社会建构主义者将客观性或真理嵌入到其社会、历史、经济和语言语境中,广泛地认为没有确定的真理,而是通过语境的眼睛对真理的感知。跨多个学科的女权主义和文化少数民族学者阐明了传统西方哲学或科学的基本原则,如果它结合了非主流观点,将会如何改变。环境哲学关注的是社会如何面临与环境互动的转变的挑战。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催生了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发展。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理论的分支,旨在帮助理解高度复杂的系统(Reigeluth,2008)。“他们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系统明显混乱或不可预测的行为之下,有某些模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又影响系统的行为”(Reigeluth,2008,p14)。混沌理论的主要特征包括协同进化、不平衡、正反馈、扰动、变换、分形、奇异吸引子、自组织和动态复杂性。
后现代主义也催生了心理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治疗的新模式。积极心理学运动和解决方案导向和叙事性家庭治疗模式是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外文文献出处:Christenson S L. Reschly,A L.Handbook of School-Family Partnerships [M].New York: Routledge, 2010,407-418.
附外文文献原文
FUTURE DIRECTIONS IN FAMILYSCHOOL PARTNERSHIPS
CINDY CARLSON
There is remarkable consensus across the chapters in this volume about several important themes relevant to family-school partnerships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 Family- school partnership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optimization of childrenrsquo;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b) An ecologic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s a usefu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complexity and importance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c) Diversity characterizes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the nation, the public school population of students, and is salient to every aspect of the educational enterprise including family-school-community partnerships; (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s valued, and we continue to have important limitations to our knowledge base regarding effective family-school partnerships. The shared voice and vision of the authors is compelling and lends credence to the prediction of Weiss and Stephen (this volume) that we are poised as a nat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a critical window of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olicy, “to realize a vision for a strategic, comprehensive, and continuous system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that demonstrably contribute to childrenrsquo;s development and school success” (p. 449).
Although the consensus that is evident in this volume among the authors is hopeful regarding the improved family-school partnerships that may emerge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 there are also barriers to this vision. Weiss and Stephen caution wisely that realizing this vision will require major policy and practice changes as well as new ways of conducting, using, and communicating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urthermore, there are psychological, structural, and historical barriers to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Christenson amp; Sheridan, 2001).
OVERVIEW
Historians argue that if we are to avoid repeating mistakes from the past, we must learn from it. In this chapter the four consensual themes noted at the onset will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origination in the past, their blossoming in the consensus of the present, and possible considerati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se themes in the postmodern future. Thus, a goal of this chapter is to situate the discussion of future directions in a larger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Toward this end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the economic forces that prompt educational and social chang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that develop to fit with economic forces, the impact of these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ldren in schools and on our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The Pas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odern Era
School-based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ervices to children emerg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 time that bears some resemblance to our current era;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begin here. Although the shifts between historical eras are multifaceted (i.e. soci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e driver largely is economic change that is spurred by scientific o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 onset of the modern era is linked with the shift from an agrarian to an industrial economy. The factory, with its centralized control, top down hierarchical focus, mass production, and worker as a replaceable part, epitomize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era. With a primary purpose of education being the preparation of a workforce, the factory also became the model for education in the modern era.1
Concomitant with the shift from an agrarian-based economy to an industrialized economy were dramatic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changes. Philosophically, the dominant discourse changed from a world organized by spirituality and faith to a world organized by reason, empiricism, mechanism, and materialism.The world became viewed as a place where lawful cause-and-effect reality could be understood through careful study and once understood, the nature could ultimately be controlled. Industrialization demanded a large, semi-skilled, centralized workforce; thus, there was large-scale immigr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where factories were situated and from the less industrialized to the mor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Im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engendered social concerns and problems that demanded solutions. Solutions to these concerns were evident in legislation (e.g. child labor laws, mandated school attendance), school curriculum (e.g. civics lessons, standard curriculum),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ervices in schools.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of social work, school nursing, and school psychology, as well as the seeds of family-centered practice, were all rooted in the soil of social concern that accompanied the widespread changes related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immigration at the onse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eplorable and crowded conditions of urban living, the presumed breakdown of the family as multi generational ties were broken with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and the clashing of cultures as significant numbers of particular ethnic groups immigrated, all engendered grave anxiety and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is social context social workers anticipated family-centered ecological treatment long before ecological psychology, systems theory, or famil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506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